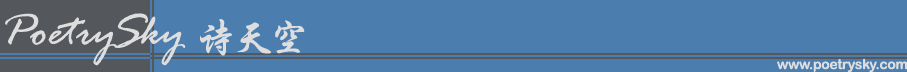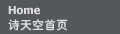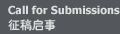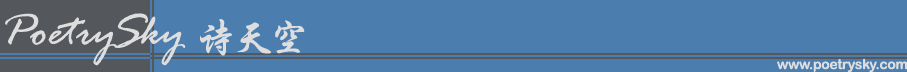殷晓媛
生于198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曾在《春华秋实》《E-zone》《世界诗人》《SAS北京人》、《中国日报》官方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文频道上发表几十篇中、英、日文作品。2006年获得《读者》原创版第十一期评刊活动二等奖。现居北京。
|

|

|
 |
一些虚伪的光线 |
一种黑暗像鲢鱼一样死去,于是
东方一抹鱼肚白泛起。地球的天阶上
坐满光头的人类,抚摸着未长满的囱门
彻夜用咿呀歌声赞美主,像摇晃在雾中的
太阳能路灯。灰色像汩汩的温泉
浸泡并漂白一些,以阳刻的方式凸现于
一汪蓝色水域间的,叫做山川路桥
的浅色纹理。一个人开始重拾
荒废掉的微笑,然后其他人受到暗示
并传递和承袭,心照不宣的惊异
黑夜没有像酸液作用于牙齿。乳白色的风
像一种流失在空旷中的沉香,在他们的缝隙中
以雪豹的威仪姗姗走过。所有举在空中的手臂
都在朝觐天女散花般垂落的光线,像一群
在日食的阴影和云层下,走得太久的剑齿虎
循着遗迹一直上溯到,传说属于他们的
冰河世纪,并天真地幻想
黑暗会像鸵鸟,被纪元和纪元之间的
耸入云霄的篱笆挡住。看!
光线多么美妙!正当他们欢呼雀跃,
一切突然又跌回黑暗,就像停电一样
光线被猝不及防的掐灭。
|
 |
愚之徙 |
我们习惯把步履托付给破折号,以为笔直
总是安全和公正的通途。踱过斑马线的时候,
深信迷彩条纹如钢条将我们框住,庇护我们
并屏蔽生命的天敌。我们憎恨黑夜
曲解我们脚下的鞋的初衷,把荆棘和芍药
都敛进柔肠百折的幽径,去惑乱光明磊落
城府不深的脚印。
我们总带着问号式的弧度转弯,尖锐陡急
似乎隐喻着宿命经络的悖逆,甚至方向的
戛然终结。我们给自然流露的深情以及
虚与委蛇的表情,都加上回旋和缓冲
的机制,以扇形和弧状的轨迹走向为美
并顶礼膜拜,将信任洒向平滑的沙滩,
却对陡狭的岬角望而生畏。
我们对省略号式的风景心驰神往。精彩唯恐拥挤,
连续恶化单调。我们信奉心脏节奏的原理
并随之一起一伏,不交替的豪迈,不断带的恬静,
都让人无所适从,挑战精神背后返祖的思想
一直作祟,我们从一棵树荡往另一棵树,
拒绝踏上林间平坦的大地。
我们总不怕找不到理由,走在前引号
和后引号截出的区间里。重力对我们推介平衡,
天地向我们灌输对称。这似乎是最佳的
非静止防御姿势,把摇篮和坟墓之间
看不见两端的长路,用视觉可以
凭倚的旗帜凸现,让我们真切的相信自己
确实在途中。
|
 |
湖是被圈养的海水 |
湖是被圈养的海水
企图用抽离了叶绿素
磨掉刺与刚毛的皮肤
取悦一个油光摇曳的慵懒种群
一群盲的野天鹅被秋天的长缨牵引
滑翔过它早就开始迟钝的生命循环
这一串意在为它加冕的铂金和钻石
却像佛的手指点下让它不敢俯仰的戒疤
海水是一种放浪的自我呼唤
暴敛了一路的温度 力量和光彩
屯蓄着富饶的血色素和白细胞
就像那种无限循环于心脏和肌腱之间的
红色速度
一路狂飚 一路大喜大悲
一些漩涡轰烈的死去 一些支流又横空出世
湖不理解海为什么总是气宇轩昂
湖总是被潮声扰得目眩气短
像血库中一袋习惯沉郁的血浆
标签上自豪地残留着某个
自体输血者经典的未雨绸缪
坚持失聪的湖听不见
海水将自己像虬龙一样掀起
又像雪后初霁的晴空一样
从淤积的冷色中将明净的光泽展开
更不会了解为什么
海穿着草鞋的足尖
总是在最锋利的崖峰上行走
像一个苦行僧兼斗士
|
 |
午夜,思想突然锋利起来 |
午夜,思想突然锋利起来,像一支
专走偏锋的银簪,以白光穿越
饱蘸血沫、柔韧而丰满的寂静,就像洄游的鳗鲡
奔向海洋一样自然。这是一个光合作用
依靠内视觉发生的时刻。一些焰火的胚芽
在极光的裙边上爆开,像火中的栗子
摊出翠黑中白的底牌,然后重复羞赧并庆幸
这是一个发条钝下来的钟点。呈燕窝状
悬在下方的地球,与它宇宙深处的倒影
以枯寂遥相呼应,用胆汁充塞并安慰一些
因徒劳断喝而上火的喉。它们
像屡经针灸而疲惫的穴位,凝固在一个
被釜底抽薪而失重的姿势上。而它们的主人依偎在
不属于自己思想体系的混沌里,讲着呓语
用树枝挑衅它们,把它们想象成
敌人的号角。
|
 |
七月游过量筒 |
穿针引线,七月像铜黄色的水银
悬挂成星陲,四处游走的透明影子
和笔直如针的气流,互相穿越
像迷走的火焰和潮水,完成虚幻而热切的
拥抱,然后赤脚踏过铺满
热煤核和玻璃渣的沙滩,默然潜回到
篱笆和堤岸后面的季节。聒噪的得意
和失意的笑声,像收紧翅膀的醋栗色
乌鸦,一路跌跌撞撞呛着水漂过
旱季蜡色的原野和空白。一个
站在构想的伞形树冠之下的女人,像一只
红色的苹果,等待久已消遁的重力
像嘀嗒钟声一样发生。
|
 |
柴檀之赌 |
黄栌色秋风下,案端的族谱像龟筮
骤然揭开。一双披着白霜的眉眼
徐徐从时间的迷谷升起。残灯摇曳
一些弥漫的线索腐草为萤。他听见
遥远的谶语从上游传来。千年以前
他的祖先受到仙人恩泽,从此困惑和懊恼
却接踵而至。仙人感动于这位花匠再三恳求
而赐予他两株植物,代价是减少三十年寿命,
他奉命将它们均种在自家庭院,但只有其中
他选择的一株,才属于他自己,
而另外一株,一道从此只能观瞻不可触摸
被他自己禁止的风景,将会在一千年之后,
向他的后裔解开这场赌博的谜底。
一株苍翠欲滴,一株盘曲古怪,
一株袅然含苞,一株清峻嶙峋,
他终于为前者投下赌注,可这场远未盖棺论定的抉择
就像两只不能开启的百宝箱,从此囚禁了
他有生之年的快乐。那株花并没辜负他
三月就开出金灿灿的奇葩,飘满砚池和葡萄架,
而他坐在窗前眼神迷离。四月山花丛中
它卸下的紫红叶尤其魅惑,像夕阳中的蜻蜓
在屋檐和秋千边流连——而他沉郁不语。
五月,蓝底红边的新叶爬上梢头,
他面前的宣纸上,墨迹却一天一天迷狂
像凌乱的舞步。六月它又捧出银色花朵,
七月风铃般欢笑的果实宛如红宝石,八月
果实成熟、醇香如蜜,而嫩枝
长出飘带一样的根,并随风降落
到每个可以生长的地方,繁衍成
只属于他自己的魔法森林。而他的抬头纹之后
笑容早已销声匿迹。尽管另一棵谦卑的植物
一直和时间一样静止,他却无可救药地预感
自己被假想误导,仙人的答案怎会让他
如此简单的猜中?一千年沧海桑田,
一千年波谲云诡,等待着的将是怎样的讽刺
他已经没有勇气想象。每缕生机蓬勃的芳香
都像是谎言的折磨;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都变成厄运来临前的平静。他坐在
花团锦簇中间,愁云满面,长吁短叹,
终于有一天,他被葬在
他那株无辜植物的花朵中间。
如今,这株一度旺盛精彩的花
当然早已归于死灭,而另外一株不出所料
长成一棵举世无双的柴檀,屹立在
寸草不生的铁锈色荒原中央。他的后裔
坐在假想中花的遗址和柴檀之间,看着十月的天空
在烟火色的西方暮下来。他听见一个声音说:
你在为你的祖先懊悔吗?他说,
不,我只是替他不值,为什么要为了
一千年以后的结论,平白错过了
一世的春光旖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