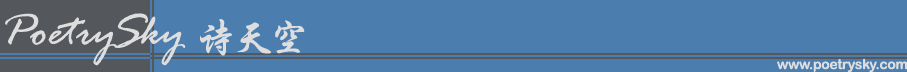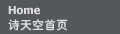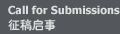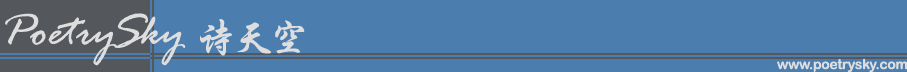李冬春
李冬春,白族.14岁在《思茅文艺》发表小说《莽莽中》。先后在《民族文学》《诗刊》《滇池》《边疆文学》等刊物及网络发表文学作品。作品入选《多种选本,《糯扎渡》获2007年度“边疆文学散文奖”、《那一年,那一天》获“滇东南文学优秀小说奖”。1995年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拉木鼓》。曾做过报刊编辑、电视记者。现居云南普洱市。
|

|

|
 |
听钢琴曲《玛格达伦纳》
--致吉奥范尼 |
一双手,突然让黑白琴键跳动
仿佛无数双手,突然从里面捧出一弘暗藏的水
在明亮中闪出美丽,激越中熄灭灯火
这“唯一的秘密,”把世界从珠穆朗玛峰最高
一一卸下。我看见青草、无名野花,不问世事的羊群
伴随湖泊和雪原,在宁静的眼睛里,眺望本来就有的一切
音符如一只,接一只,最终成群飞向天边的云雀
在它们的国度,飞翔是自由的,骄傲也是必要的
吉奥范尼。一个始终没有背景与肖像的音乐家
不知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他是把云雀放飞
并执拗地化身为羽的其中一个,他也在飞,姿势明净
在那样的高度飞翔,如果像风,那就是风
风拂过大地时,世界的耳朵和神经,树或花朵
全都为之战栗。听,最后一个音符,收缩到了指尖
|
 |
芦花 |
湖边。水的角落,群鸟飞动
许多沉寂的事物,突然出现
而大片芦花即将枯萎
只有历经夏的炙烤,秋的煎熬
初萌冬意里萧瑟着的一片芦花
才会引来一次意外的关注
世界的脚步,总是姗姗来迟
美丽属于花朵。呵护,芳香,赞美,也是花朵的
谁在乎芦花那经年积累的一点卑微、脆弱
无人知晓的落寞,独立风霜的守望?
狗尾巴、仙人掌、老鸹花、鹿衔草……
一切不知名的,黯然、暗淡、轻易便被践踏
被遗忘和忽略的芸芸众花
尽管也曾萌动,摇曳,也曾唤醒春天
唤来蜜蜂和蝴蝶。执拗地,把卑微一次次点燃
终究不能避免,无数次,宿命般的熄灭
微风拂过,世界不为所动
就在一刹,在风的手指刚要触碰的一瞬
早于落英,满眼芦花突然缤纷
那片不让染指的,似乎从未存在的白色
一下子活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
 |
是雨,总要下落 |
天气转阴,又一个生命被雨点送走
如果从未与逝者认识
此刻我不会在意天气。对忽然降临的冷
也许会有感激。热闹的人间,需偶尔冷场
有时我走到墓地,不为别的
只是看一眼林立的墓碑,默读一个人的一生
简化为寥寥数字。活着承受人间风雨
死去同样背负泥土、石头,几蓬枯萎的草
世界总在轮回,生命永远只出现一次
那逝去的、过往的种种,还会回来
以泥土、草、树木,或一阵风的样子
西边、南边,在我们看不见的任何地方
来来往往,死而复生
这一切都不重要。下雨了
一个人的生命,随之落下
落在土里,落在心里
簇新的泥土散发着
雨水透明的味道。是雨,总要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