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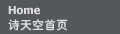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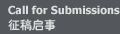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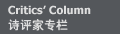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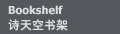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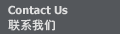 |
| |
蒙古国诗人森道哈达专访
森道哈达住在乌兰巴托,任教于蒙古国立大学。
作为经常去中国参加文学活动的蒙古国著名诗人,森道哈达对当代华语文学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他说,亚洲诗的未来在于继承优秀传统。他渴望复活东方的诗歌精神。蒙古的山脉,平原,戈壁,森林,湖泊,河流以及牛马羊骆驼,是他灵感的来源,雅托克竖琴像流水的音乐进入他的心灵。让我们和诗人唐朝一起走进森道哈达的内心世界。
唐朝: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诗作? 哈达:每写完一首诗,我为自己的新作品诞生而感到欣喜。两天过后当我再拿起它时又会有一种不甚满意感袭来。在诗歌写作上,我慢慢发现我喜新厌旧。诚然我能用眼睛,心,气感悟自己的作品,用对比和时间来反思自己的作品,但更愿把评价自己诗作的工作交给评论家们。 唐朝:您是否觉得您的诗是越写越好呢?您最喜欢自己的哪首诗?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创作经历? 哈达:每当我在看过去我写的诗,我最大的惊喜就是感到自己的诗越写越好。写作时我喜欢心到手到,顺其自然,决不无病呻吟。我喜欢自己的一首短诗《杭盖》,长诗《上都悲歌》。我愿借此宝贵机会展示《杭盖》: 在天空平坦的北亚细亚/ 居住着高原色的普氏野马/ 绿色是杭盖的颜色
(注:在欧洲,蒙古马被称为普氏野马。这是以俄罗斯博物学家(Equus przewalskii)尼古拉. 普尔热瓦尔
杭盖( Hangai ),一个古老的蒙古语单词,它的意思是,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山和森林的世界。) 难忘的写作经历并不少,这里因篇幅只谈一经历吧:那是三年前,我赴景色秀丽的漳州-出席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各国的学者探讨林语堂的文学遗产和价值。我初次走进林语堂的故居和文学馆,感受良多。记得我被安排坐在8 号Bus 上。一个含羞带笑的学生样女子自我介绍作全程导游。每到一处,她总是跑在最前面,为大家解说风土人情和林语堂的童年等,有时完全是与学术无关。我跟在她身后。有 时我离她很近,就象小学生在听一位年轻女老师讲课。天气有些闷热,我几次看见小汗珠从她的脸颊滑落,可她没说过一声累字。从清晨至日落,我发现她的微笑永远那么美,永远洋溢着青春。后来我回到蒙古高原,想起漳州,就想起她那微笑。微笑就是一首诗: 妳的笑容 我
妳
唐朝:您认为诗是否应该有其社会意义?还是仅仅反映个人的心声?诗人应该担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 哈达:啊, 您问的这几个都是大题。不见得衡量一首诗非要看它是否应该带何社会意义,诗既然是人写的,就必无法逃避社会。可是诗毕竟是高超意象语言的写作艺术,诗人写作完全是个人的写作。即使被认为它再现了一个时代或超越了时代也完全是诗人灵魂的声音。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甚至数字化时代,一个国家打仗已不再与邻国无关,发射原子弹,动用核武将危害全人类。人的本性有贪婪,好战的一面,但爱好和平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诗人是最具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类人,憎恨战争,热爱和平,自由和爱情。 唐朝:请问您创作的动力是什么?蒙古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哈达:动力一是活着。动力二是为什么还活着。动力三是活着就有理由写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是蒙古人。蒙古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自然对我的创作影响很深。蒙古是典型的草原自然地理,在碧蓝的天空下,是山脉,平原,戈壁,森林,湖泊,河流,与人类最和睦相处的牛马羊骆驼等生灵,在北部还有牦牛和麋鹿。尤其是游牧蒙古人世世代代居住的蒙古包,神秘的岩画,蒙古长调民歌,呼麦喉音,如万马奔腾的马头琴乐器,雅托克竖琴像流水的音乐进入我心灵。我成长在这片与自然和谐的土地上,好像天地万物与我共生。我的恨远远不及我的爱! 除了自然给我以启迪,任我尽情拥抱的是辉煌灿烂的蒙古古典文学和美学。而现代社会环境并不尽人意,这也是我面对的现实,我的写作不会逃避现实,灵感时常来临于我孤独与沉思的一刹那。 唐朝:哪些诗人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哈达:除了蒙古历代前辈诗人外,我较早开始偏爱叶赛宁的抒情诗,早期作品有他的影子。其次是一位瑞典诗人马丁松,他的诗意-游牧哲学观与我的潜意识写作不谋而合。当我渐渐变得在诗艺上成熟起来,我知道我不再被某一诗人轻易影响了。读里尔克,兰波,读帕斯,甚至读活着的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包括新崛起后现代诗人们的诗时,我也很理性,我还是我。 唐朝:您喜欢哪些华语诗人的作品? 哈达:如果是问当代华语诗人,其实我读的太少。在现代诗方面,从诗艺来说,我喜欢艾青的两三首抒情诗。徐志摩的一部分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突起的创造性的华语诗人,非常值得我们敬重。我越来越喜欢更自由明朗,更具忧患意识,也更现代的华语作品,象骆英的《小兔子》。田原的作品《枯树》、《作品一号》,旅美华语女诗人绿音的作品《租借幸福》、《与空杯对饮》我也非常喜欢。 唐朝:您最喜欢哪些欧美诗人及其诗篇? 哈达:喜欢欧美诗篇,很多时候只是短时间里。长时间喜欢的还是诗人的思想人格魅力。他们备受苦难的命运成为鼓舞我前进的驱动力。在欧洲,我更喜欢早一些的但丁,瓦雷立,黑塞。后来的意大利诗人夸西姆多。在北欧我最喜欢索德格朗,美国当代的罗布特-布莱,我也翻译过他们的诗用蒙古语。他们的诗篇是世界诗歌艺术的财富。原谅我没有准备作品的名字。 唐朝:创作中如何掌握诗的韵律和节奏? 哈达:一首诗的韵律和节奏很重要。在蒙古语诗中必须每行押头韵,十分注意控制诗的节奏感。蒙古诗人朗诵诗好像是在唱歌的感觉。我写诗时更喜欢不拘泥于格式,让感觉流动,节奏越自然越好。当然我有不少诗也是押头韵的,但这不是我作品的整体诗风。我敢说,好诗一定是考虑了诗的韵律和节奏的。 唐朝:您经常去中国参加文学活动,您怎么评价中国的诗歌现状? 哈达:是的,我出席过几次文学会议,诗学论坛和笔会。结识了许多资深学者,大学文学教授,著名诗人和作家。我的感觉是他们的观点很开放。学院派的观点多趋保守一些。每次去中国参加文学活动我都会受益很多。因为我并不需要有中介当翻译。我受到友好和真挚接待。感受到文明古国的现代文化丰富而开阔。谈中国的诗歌现状,这是诗学课题。我可以把它带到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展开学术研讨。我还是愿对中国的诗歌现状抱以冷静观察,他仿佛已走到一个阶段,需要转向新的,更令人期待的阶段了。延续现状,还是突破现状,正是中国的诗歌现状的现状。
2010年2月5日 |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