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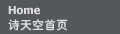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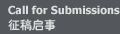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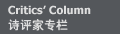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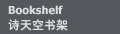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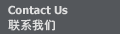 |
| |
诗人夏菁访谈
夏菁,是盛志澄的笔名,浙江嘉兴人.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一生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夏菁诗歌创作50多年来淡泊名利,默默耕耘,最近又出版第十本诗集〈《独行集》。他始终把诗作为其“终身的追求”, 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梦”。诗人夏菁近日接受了诗人绿音的采访。
绿音:作为台湾 “蓝星诗社”创始人之一,您认为诗是否应该有其社会意义?还是仅仅反映个人的心声?诗人应该担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 夏菁:诗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诗人不能睽离社会。我当时发起 “蓝星诗社”及主张诗人应抒发个人的心声,主要是针对当时台湾政治挂帅、大家摇旗呐喊的一种反抗。我希望诗人不要淹没在一种流行的歌声中,齐声合唱,扼杀了创作的独立性;而应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内在的声音。写诗犹如恋爱,由诗人自己选取对象,不应由人匹配。 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生活方式、环境、工作不同;学养、个性、思想和感受也互异。只要各自忠实地去表达自己就行。如果社会各阶层的诗人都能如此,就不乏激昂的歌和婉约之音,就会自然而然地反映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精神。这是多元社会的基础,也是民主的真谛。因此,我个人认为:诗人如能尽一己之力,表达自己的心声,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有所贡献,就应该算是担负起社会的责任了! 绿音:1968年您离开台湾到联合国工作,成为知名的水土保持专家和教授,但您在美国、中美洲、泰国等地住了40 多年仍保持创作热情,请问您创作的动力是什么?国外的自然环境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夏菁:我从 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起到1968年离台以前,已出版了四本诗集,平均四年一本。但在初到联合国工作的六、七年中,因工作太忙、压力太大。记得那个年代,又遇到晦涩或朦胧诗盛行,我就韬光养晦,诗也写得很少。许多诗友们认为我已才尽 (literately dead)。但他们忘了我早年说过的诺言:“诗是我终身的追求。” 到了1975 年,我又恢复写诗。那时“蓝星诗社’正推出新型的刊物。我常说,组织诗社的好处,是相互维系和激荡,不在彼此的标榜。我和诗社同仁,半世纪来一直保持联系,不论身在天涯或海角。此后在美国的二十五年中,我的诗除在蓝星及港台的诗刊发表外,北美和台湾的报纸能够经常接受,也是一种鼓励。《诗天空》网刊的出现,又激发了我对翻译诗的热诚和兴趣。足见,具有发表的园地,对诗人是何等重要。 至于身处国外对创作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坏处是感到孤独和寂寞,缺少了那种煮茶论诗的快感,作品当然也会减少。好处是视野广阔、中西作品都可看到。而且耳目清净、不受国内那种时髦和流行的影响。可以一心走自己的创作路线。 绿音:您数十年来,不论在何处,本身工作都很忙。上山下海、写书、撰文、参加国际会议,以及教育培训等等,您如何能在职业和写作间谋取平衡和成就呢? 夏菁:现在能靠写诗为生的人,无论中外,均绝无仅有。大多数是业余诗人。但业余诗人中也有职业上的分别。教授文学及文化工作者,日常和诗文接触,念兹在兹,激励写作的机会就多。像我这般做着和写诗无关的职业,工作繁忙,又僻居海外,当地几无诗友,有时的确觉得难以为继。我不敢说对诗负有什么使命,只是想保持一种兴趣,一种追求而已。当周末及假日别人去打球、玩牌、跳舞、喝酒;我则偷闲去看书或写作。我的创作不算多,只是细水长流。心中有一点火苗,有一个梦,持续地摸索前行。不计其他;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一向是我创作的态度。 像我这样的业余诗人,比起以文学为职志的诗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没有压力。写作在我是一种升华、一种欢喜、一种变奏,像一具精神上的翘翘板。如果在职业上受创,我可以在写作上升空。反之,也可以在工作上落实。没有包袱、也无野心。我曾说过:写作是生活上的调节, 一种欲罢不能的赴约。 可是,我一直在怀疑,也在抱憾,假如我集中只走一条路,是否会较有成就呢?我不知道。 绿音: 想像力是诗人的财富,您是如何发挥您的想像力的? 夏菁:一般而言,多读、多看、多思考,是培养想像力最基本的条件。吾国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说;也有行万里路之议,那就是出门去多看、多经历。名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曾言:我们的想像力,一部份源于书本,大部份产自诗人一生的经验。说得很对。但我认为,经验人人都有,一片湖边的水仙,一只冬夜的画眉、一座雪夜的森林,都是常见的事物。唯有大诗人才能写出不朽的作品,为何? 这就靠吾国诗论中常说的 “悟”。 “悟”并不神秘。我曾经解释: “悟”就是 “想像力的贯穿”。多读多看还是不够,要多加思考,才能获致。学而不思则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姜白石说: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我想,诗人不寻常的作品都是悟出来的。他们用想像力贯穿事物的表面,获致内在的真。这种真,并非现实世界的真,乃是使读者在瞬间能够相信的真 (A world of make-believe)。诗中能使“海沸腾,猪行空”,不是吗? 西方谈诗,常说“上帝给你一句句子。”以我看来,这就是你个人经验 (包括读和看) 的反刍。其余的部份,你要和上帝或天使去“角力,”才能完成。所谓角力,不就是深思吗? 我自己的经验,在为世俗奔波之日,为工作忧虑之际,鲜有诗绪。只有在心情开朗、无所牵挂、或休闲、自在之时,常会有灵光一闪、眼角生情、诗绪油然产生。我就坐下来,集中精神、反复思考,将之发展成篇。这往往还是初稿而己!我从前说过,诗人的雷达网,如果关闭了,则灵光即使在头顶闪过,也会视而不见。 绿音:您是否觉得您的诗是越写越好呢?您最喜欢自己的那首诗?有哪些令您难忘的创作经历? 夏菁:每个诗人都会觉得刚完成的作品,有新意,有突破,希望拿出去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 “小儿子情结。”但时间久了,经过冷静的判比,也许看法就会不同。以我而言,我觉得自已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些自己喜欢的作品。这些诗也只有二十首左右,为数不多,大多已选在各种诗选之中。我觉得生也有涯,一生的努力,如能留下一、两篇让人记得的诗篇,为这个时代留些雪泥鸿爪,已属万幸。唐诗五万多首,我们能记得多少篇呢?迄今我还是个过河的卒子,靠一点自信,努力向前,不计好坏和成败。 当我在多年前写一首千行长诗 《折扇》时,的确有不少难忘的经验。这是一首自传式的抒情长诗,涵盖四分之三个世纪 (1925 年到 2001 年)。要写得忠实、不违事实;要写得赋有可读性,不是流水帐;要写得像诗,不是分行的散文;要写得叙事不忘抒情,能使情与景并进;又要表达个人的观感和时代的意义,实在是一桩严格的挑战。我虽然曾写过两本诗剧,但写这首长诗,我花的精力和时间最多。前后写了有两年半之久。我不知道最后有否达到我自己订立的标准?有人说,写长诗可以考验一个诗人的能力和耐力,实非虚语! 绿音:古典和当代的诗中,您喜欢哪些华语诗人的作品?他们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夏菁:像我同时代的国人一样,年幼时都念过唐诗,我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都很喜欢。渐渐,对陶渊明、王维、杜牧、以及李商隐的诗,有所偏爱。我自忖不是文科出身,杂学无章,全凭一己的兴致。但对古典诗用字的简约、意境的深远,在幼时已铭刻在心。只是觉得格律严谨,难以效法。 稍后接触到新诗,读了新月派及创造社的诗,觉得诗体和语言,自由得多了!因此,也有跃跃欲试之想。那个时代的诗人是吾国新诗的先驱者,对我的主要印象是要自由地、忠实地写,不要无病呻吟。 我对抗日战争以来那些激昂的诗,确感到热血奔腾,但读多了,觉得千篇一律。后来,诗沦为宣传的工具,更是不堪卒读。如前所述,我的发起 “蓝星诗社” 主张恢复诗人抒发一己的心声,原因在此。至于台湾同仁及诗友中的作品,有不少我很喜爱,也互有影响。但因篇幅有限,不欲例举。以免举一漏百,或有标榜之嫌。至于六O年代以来流行的晦涩诗或朦胧诗,关闭了传达的大门,对读者不公平,我不喜欢。我一向的主张是:诗要有可读性。当今 “后现代的诗”,理论各说纷纭,作品优劣杂呈;抒发一己,确是好事,有些过份琐碎,是否受人欢迎?尚待时间去沉淀和挑筛。 绿音:您最喜欢哪些欧美诗人?翻译欧美当代诗歌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夏菁:在五十年代末我开始接触到欧美诗。最初,我很喜欢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的那种长短句,清新洒脱,窥伺天机。我在1957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 《喷水池》里,有节有韵,几乎全是这一类诗体。其中一首《月夜散步》,现被广泛选读,即是那段时期的产品。几乎在同时,我爱上当代美国诗人佛劳斯特 (Robert Frost) 的诗。对他的 “一首诗始于欣喜,终于智慧。”(A poem begins in delight and ends in wisdom) 的说法,一度奉为圭臬。他用口语入诗,读起来亲切而有节奏感;深入浅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句子看是平易,整首却意味无穷。他的诗作,可以说,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性。当然,任何诗人的创作,均基于他一生的学养和经验,不会全凭一家之言。其他,如叶慈 (W.B. Yeats)、哈代 (Thomas Hardy)、浩司曼 (A. E. Housman)、劳伦斯 (D. H. Lawrence)、以及近代的史奈德 (Gary Snyder) 和罗伯特-布莱 (Robert Bly) 等的诗,我也很喜欢。 译诗需要细读原作,斟酌两边文字,费煞考量,当然对译者的写作会有影响。而且,吾国的新诗,还在发育和成长时期,翻译欧美的诗,对整个新诗的发展,也大有裨益。我虽翻过几个欧美诗人的诗,并无系统。其中如佛劳斯特的六首,被选入1961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诗选》中,感到很是荣幸。但自己总觉得时间不够、力有未逮。现在用英文翻翻自己的作品,已感到尽了一份棉力了。 绿音:中美诗歌交流的意义何在?《诗天空》(PoetrySky.com)即将创刊五周年,您有何寄语或感言? 夏菁:诗歌和文化的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要有人认真和持续地去做。吾国的新诗,尚在开拓时期,需要借鉴欧美作品的地方很多。在另方面来看,华语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很多中国优良的传统和内涵,可以让世人有所认知。现在是地球村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快。不少西洋人对吾国文化,深具兴趣。英美现代诗的先驱庞德 (Ezra Pound) 不是很醉心我们的文化和诗吗?虽然他不甚了了,却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译得多了,中国的诗将是欧美诗的一大刺激品 (a great stimulus)。 《诗天空》不是一个官方资助的团体,以其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在中美诗歌交流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华语诗人和一些著名的美国诗人的热心参与,确是难能可贵。 值兹《诗天空》出版五周年之际,我衷心期望它能十年、廿年、卅年,甚至更久地持续下去,使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为吾国及世界诗坛,作出贡献。 我也希望《诗天空》除每季按时出版网刊以外,也能赓续及扩大地出版个人诗集(包括双语),以及选集、合集等,以广流传。在人力、财力充沛后,盼能恪力推行进一步的文化传播活动。
|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