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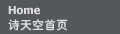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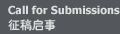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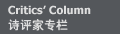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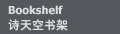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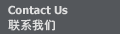 |
| |
夏菁 Hsia Ching
夏菁,是盛志澄的笔名,1925年生于浙江嘉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硕士,曾任联合国专家及科罗拉多教授等职。夏菁是台湾 “蓝星诗社” 创始人之一。自1954年 出版第一本诗集起,已有九种,包括近年出版的《雪岭》(2003)和《夏菁短诗选》(2004)等。 Hsia Ching, the pen name of Ted (Tse) C. Sheng, was born in Zhejiang, China in 1925. He received his M.S. degree from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1966) and has work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aught at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Hsia Ching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Blue Stars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in early Fifties. Since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published in 1954, he has produced a total of nine volumes of poems including the recent two: A Snow-capped Peak (2003) and Selected Poems of Hsia Ching (2004).
|
除夕談往:心靈的對白除夕傍晚,紅霞在天,積雪滿地。忽然有一個黃衣的不速之客,在我昏暗的書房裡出現。他開門見山地就說:你生於乙丑,明年是你的本命年,要格外當心。我正在唯唯時,他又問:你一生有什么遺憾? 被他突然一問,我倒是一時答不上來。回想我這一生,少年時確吃了些苦,成年後卻是柳暗花明,一路走來,受上天特別眷顧。我回他說:沒有什么遺憾,我此生已發揮到百分之一百二十! 他滿臉怀疑地追問:這話怎么講? 我答稱:我幼時身體羸弱,現已活到八旬有四;我早年在台專心工作,並無出國的夢想,卻為聯合國聘用;我只有碩士,能在美國大學教研究所;我不是學文出身,也有十數本詩文集出版;我…….. 他沒有聽完,就說:能否說得具體一些? 我說:在十二歲到二十歲間,適逢日本侵華,避難各地。當時生活艱苦,清粥淡麵,有甚滋養?其間染上瘧疾,也無良藥,因此身體瘦小羸弱。記得我在二、三十歲時、體重還只有一百十六磅 (五十二公斤)。所幸後來有太座照料,注意健康,起居有律,尚能東遷西播,到處工作。六、七十歲時曾意外地斷腿、折腕,和最近的庖疹,也都安然度過,平時也不服藥。若非上天眷顧,豈有今日? 那末,在職業方面有何遺憾? 我答稱:在這方面我更無遺憾。在台灣時,我在一個中美合作的農業機關工作。這是全台農業的最高單位,聲譽好、效率高、工作環境特優、待遇也好。在那裡,不但可以學以致用,而且可以一展所長。後來我應聘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在十七年中去了很多國家擔任專家或顧問,也都很受人尊敬。在羅馬總部的主管單位,曾兩度提名我為傑出服務得獎人,但因那時台灣已退出聯合國,受了政治影嚮,而未獲當選。但我在FAO 出版的幾本英文專刊,卻被譯成西班牙文及法文等等,在全球發展中國家普遍應用。後來,我在一九九一年獲得美國水土保持學會的最高獎 :班乃德獎 (Hugh Hammond Bennett Award),覺得更為榮幸。因該學會有一萬會員,遍佈全球,而且大部份是教授和專家。我是該會成立五十年來第一個亞洲人獲此殊榮。我在二OO五,又得了在台北的中華水土保持學會終身成就獎。 他接著又問:那你到美國的二十多年間是否都如意? 是的。我在此間的母校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執教十年多。我雖然不是博士,但我用的是我自己的著作、及我在世界各國的實地經驗來教導博土、碩士研究生,也頗受歡迎。而且,同事中有我早年的同學,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自卑感。離職時,大學還給我榮譽教授的名義。在此執教時期及嗣後五年中,我賡續受聘于聯合國、世界銀行、美洲組織、美國援外總署等等擔任短期顧問。直到二十一世紀,我已七十五歲時才真正退休在家。 說的雖都是事實,但他還要追問我的遺憾之處:那你的家庭生活怎樣? 我說我的家庭,素來和諧美滿。妻子聰慧賢淑、謙和勤儉。她很樂觀、也明理爽直。是一位最佳的伴侶;我們也活得像 一對無邪、快樂的孩童。對兩個兒子,我們素重身教而輕言教。早年在 <純文學> 上有一篇小品,說我管教兒子形同老莊。此言不假,在孩子成長時,管教難免有些棘手。我忙碌在外,她又是菩薩心腸。但後來他們都得了博士,成家立業,體貼孝順。所以也沒有遺憾可言。 忽然,他像記起了什么,向我問道:你在文學方面,好像有些遺憾,不是嗎? 也不能完全說是,我說。我不是念文學出身。但在年輕時和幾位詩人發起了一個在台灣很有名的 <藍星詩社> ,主張祟尚抒情和自由寫作。這個詩社五十年來出版了四、五百本期刊、及個別的詩和散文集;不少同仁,已是當今文壇上的翹楚。我自己也陸續出版了九本詩集、四冊散文。 到現在,我還持續在北美及台灣的中文報紙及雜誌撰寫詩文。手頭還存有詩、文稿各一,正尋求出版。我知道你所說的遺憾,是指我從未得過什么獎。是的!一方面,因我離台已四十年,文壇及讀者對我難免生疏;另一方面,我也不願和年輕人去爭一時的名利。詩、文是千秋大業,任其自然,也不能算是遺憾! 他忽然笑道:不要說得太嚴重了!讓我來問一個輕鬆的問題:你有沒有寫過像 <蓮的聯想> 那一類的詩? 我說:很久以前曾經寫過,現在則偶 一為之。我又告訴他,我有一次問起余光中:你寫的這束詩,是否確有其人其事?光中用英語回答我說:” Mostly exaggerated.” 我很後悔,不該問他。我暗想:所有的文學作品,不都是這樣產生的嗎?詩人賦有出神入化的想像;又具捕風捉影的能力。只要是 “發乎情,止乎禮” 寫這類詩,有何不可!詩人一生如果在這方面繳白卷,反而是一大缺失。雪萊曾經說過 “詩人的日糧是愛和名聲” ( Poet’s food is love and fame),對嗎? 他聽了,好像很滿意。但到最後,他還回到原題、用委婉地口吻問:你一生難道真的沒有走錯什么路嗎?我坦然地回答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走了兩條分歧的路,想在文學和科枝上均有卓越的成就。假如只集中於 一條,也許………….. 話未說完,這個黃衣人已在我眼前消失,去得無影無蹤。我看看窗外車道,也無車痕或腳印,只聽到一陣冷風在窗前掠過。 (原載《世界日報 》) |
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