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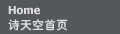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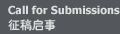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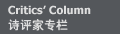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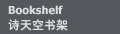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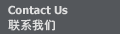 |
| |
夏菁 Hsia Ching
夏菁,是盛志澄的笔名,1925年生于浙江嘉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硕士,曾任联合国专家及科罗拉多教授等职。夏菁是台湾 “蓝星诗社” 创始人之一。自1954年 出版第一本诗集起,已有九种,包括近年出版的《雪岭》(2003)和《夏菁短诗选》(2004)等。 Hsia Ching, the pen name of Ted (Tse) C. Sheng, was born in Zhejiang, China in 1925. He received his M.S. degree from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1966) and has work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aught at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Hsia Ching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Blue Stars Poetry Society in Taiwan in early Fifties. Since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poems published in 1954, he has produced a total of nine volumes of poems including the recent two: A Snow-capped Peak (2003) and Selected Poems of Hsia Ching (2004).
|
詩人難為我們常說做人難,其實做詩人更難。美國著名詩人佛勞斯脫 (Robert Frost) 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不勸人寫詩,這是自掘墳墓 (That ought to be one’s own funeral),生活會非常、非常地艱辛。我想,古今中外,以寫詩為生的人,絕無僅有。都是要靠其他職業來維持生活。最近,報上有一則消息,說是湖南有一位詩人,因不想 “每天寫詩的時候還想著下一頓吃什么” ,而宣佈 “希望有富婆或富姐包養”。聞之使人哭笑不得。 年輕時每一個人都喜愛詩;戀愛時寫寫情詩,好像都可能成為詩人。但要維持這種詩心、童心,熱心,繼而成為一個詩人,實非易事。我早年在台北時,遇到一位年輕人,他偶然在報上發表一、二首詩,就要辭去工作,專心寫詩。我勸他不必如此,他不領情。後來聽說他一邊寫詩,一邊不得已在淡水河挑砂石為生,令人欽佩。 我的已故詩友鄧禹平,寫過電影 <阿里山風雲>的主題歌: 高山青。在那時台灣、幾乎人人會唱,而且歷久不衰。他在1950年左右自費出版了一本抒情詩集 <藍色小夜曲>,在當時政治掛帥的气氛中,清新脫俗,耳目一新。但還有一批人說他是浪費感情,使他覺得詩人難為。不久,他和我及余光中等發起了一個詩社,就是要相互鼓勵自由創作。有一次,我們談到寫詩的甘苦和社會的冷淡,他送了一首小詩 <釣愚 (魚)人>給我,有一段如下: 小魚兒就像我們的詩呵!
那末,市面上一首詩究竟值多少錢呢?當時大多數的報章雜誌、都不接受詩,如果僥倖刊出,也不給稿費。只有極少數的報刊,付給酬報。以我的記憶,在1950年代,一首十多行的短詩大約是新台幣30元 (合美金 0.75元)。到了80年代,每首約為 800元 (美金25元)。迄至今日,沒有增加多少,因為報刊自身面臨很多挑戰之故。一首詩修修改改至少要費三、四天才能完成,以此計算,則每小時的報酬約為一塊美金,只及麥當勞小女孩工資的六分之一!當然,有人會說,詩的价值無限,豈能用金錢來衡量?聽慣這樣的美言,詩人也只好像過河的卒子了! 寫詩如不計較酬報,剩下來的就是要名吧!那也不盡然。對詩人來說,名是如此地虛無飄渺,不可捉摸。現今社會上名人、名媛、名星充斥,誰希罕寫詩的人?而且寫詩的也不會一夕成名。正如美國名詩人兼評論家賈拉爾 (Randall Jarrell) 所說,除非詩人殺了老婆 (可怕!)。 我在一般人前,常隱藏起詩人的虛銜,因為這並不能增加別人對我的敬意;反而給人一種不務實際的錯覺。詩人住在瘋子的隔壁,這可是一般人的先入之見啊!說到名聲,我有許許多多的詩友,都得過大大小小的詩獎。而我呢?從不去申請、從不與人競爭、從不和文化機構打交道,而且已離國四十載;因此,這種所謂 “十五分種的名氣” 不會平白落在我頭上──雖然,我還在繼續追求繆斯。以下是我戲作的一首墓誌銘: 這裡趟著一個詩人,
我現在寫的詩,能在國內外中文報紙及刊物上經年、陸續地發表,已該滿足了!酬報則在所不計。只是有時我的詩被誤植、誤印,覺得非常懊喪,好像當眾未扣好褲鈕一般, 奈何不得。例如,我有一首詩: <月夜散步>,被收入<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中,由台灣一個頗有名望的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寄來以後,發現題目被誤刊為 <月色散步>,我覺得不妥,立即去信更正,卻無回音,我也不知道再版時有否改正?只是最近發現,這首題目印錯的詩,一直被教育測驗機構用來測驗中學生的國文;如此連題目都不通的一首詩,怎能教測學生?真使我汗顏不已。 寫詩既無名利可圖、有時還被誤印,社會上一般人又多誤解。詩人如果沒有信心、童心、和耐心,確實難以有始有終。放棄繆斯,追求財神可也。可是有一批死心塌地的人,追求繆斯永不悔改,我是其中之一。我在195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 <靜靜的林間>的後記中,曾說過: “詩,在我是終身的追求”。為了實踐這句諾言,我在公餘、課餘、睡餘、繼續寫詩半個世紀;至於有多少成就?那就難說。 詩人難為。為甚還有這麼多的傻子像我那樣,念玆在玆,為詩而嘔心滴血呢?我只能借他人的名言來回答:詩人必須是天生和人為兼具 (both born and made)。既然一半是天生,當踏出第一步以後,就由不得自己了! (原載《世界日報 》) |
版权声明
